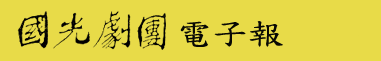|
三年磨合,認識彼此六百年的傳統藝術
--略談此次崑曲與日本邦樂的合作
林于竝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副教授兼學務長、《繡襦夢》戲劇顧問
(本文於國光藝訊99期同步刊載)
崑劇與能劇是各自擁有五、六百年的歷史,經過漫長時間的淬煉,在藝術上高度完成的劇種。讓這兩者交會,創作一個當代的作品,這個構想最初是日本橫濱能樂堂的出題,中村雅之館長從2015年即陸續來台,向國光劇團提出共同創作的意願。最先想到的,是找一個兩者故事內容類似的曲目,以兩者的共同點作為創作的出發。非常感謝國光劇團的邀請,讓我加入這個非常有意義又充滿探索歷程的工作團隊,一開始想到的是《邯鄲》,蜀國盧生在黃粱一夢當中歷經榮華富貴的故事,日本能劇用一段舞蹈動作表現春夏秋冬時間快速的流轉,一切成為過往雲煙。但是因為同一的題材被說成不同的故事,要把兩者放在一起有點困難。
為了說明日本能劇舞台以及戲劇結構的特色,我介紹了《松風》這個作品。一個雲遊四方旅僧來到了一棵松樹底下,當地人告訴他這是一對名叫松風跟村雨姐妹的埋葬處。因為天色不早,旅僧來到一戶人家請求借宿,而這戶人家的主人竟然是這對姐妹。這對姐妹面對旅僧開始傾訴,因為心中對於愛人行平強烈的思念,死後靈魂無法滅度,成為鬼魂徘徊在這棵松樹之下。松風開始述說對於愛人的思念之情,並且拿出行平當初離開時所留下來的衣服跟帽子。在傾訴生前與愛人同舟遊海美好的日子當中,松風逐漸陷入瘋狂,將行平的衣帽穿在身上,最後在舞蹈最激烈的節奏當中,倏然消失在黑夜裡。這個故事讓王安祈老師聯想到另外一個故事《繡襦記》。一樣描寫人世間最難割捨的愛情與徒然的遺憾,以及都有一件衣服做為舞台重要的道具,以此展開這段在兩座戲劇高山之間跨越文化縱谷的冒險。在橫濱能樂堂中村館長的建議之下,以歌舞伎的樂器(音樂)、能劇的舞台,以及崑劇的表演作為基礎條件,創作一齣新的舞台作品。
為什麼不讓能的樂器與崑的表演直接對峙?因為這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這是中村館長的判斷。對於各自獨立發展幾百年的兩個劇種而言,音樂不只是樂器發出來的東西,台詞的語言是音樂,表演的身體是音樂,甚至無聲的空間也是音樂,因此使用在時間上必然是以較近期的歌舞伎音樂作為介質可行性比較高。
能劇的舞台也不只是等待把表演放進去的空的空間,它本身就帶有某種獨特的看世界的方法,換句話說,能舞台本身已經制約了說故事的方法了。無論是「現在能」或者「夢幻能」,能劇的故事總是帶有某種「無常感」。觀眾在能舞台上所體驗到的,與其說是時間的經過倒不如說是時間的消逝。能舞台的後台樂屋(鏡之間)是屬於冥界(另一個世界)的空間,而主要的舞台(本舞台)是屬於現世,兩者之間由「橋掛」所連接。所有能劇的角色可以說都是從另一個世界渡過橋掛來到這個世界的存在,而所有發生在本舞台上,此時此刻的事件,都是過去的幽靈幻影,即使是現世的愛情,都是從死後的觀點來談論。能舞台的結構讓能劇的視角彷彿宇宙的凝望,從極遠的時空凝視地球的一角。
王安祈老師與林家正新編的《繡襦夢》,讓傳統崑曲《繡襦記》裡的鄭元和從不同的視角被重新觀看。生命來到終點的鄭元和回到當年他與李亞仙相遇的曲江,那是一個在鄭元和的生命裡不斷「徘徊」的地點,因為李亞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遺憾,在那裡他以當初李亞仙離開時所留下來的「繡襦」召喚過去。在能劇的《松風》當中,松風與村雨兩個姐妹其實是同一個靈魂的分身,在《繡襦夢》裡,繡襦是李亞仙的分身,替代李亞仙來向鄭元和訴說當初離開的原因。《松風》與《繡襦夢》一樣,都是一個生命停滯不前的故事,愛情是靈魂的重量,在《松風》裡,也許基於旅僧的法力,松風與村雨姐妹最後得到救贖也說不定,但是在《繡襦夢》當中,無可救藥的鄭元和卻更令人感動。當繡襦最後說出:「我不是亞仙」時,這個隻身在曲江邊的風燭殘年的身影更不知道要如何安頓他的靈魂。
最後,補充說明這項合作分為三段式的演出:第一段是傳統崑曲《繡襦記》的折子段落《打子》;第二段是日本傳統藝能舞踊,劇目《汐汲》訴說的是與能劇《松風》相同的故事。第三段新編《繡襦夢》表演以崑曲為主體結合舞踊身段,音樂除了崑曲之外,也加入日本傳統講唱形式的長唄,以及三味線大師常磐津文字兵衛的三味線演奏。日方以「邦樂」稱之,大略等同於我們以「國樂」泛指傳統音樂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