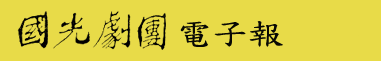|
||||
|
||||
|
國光電子報 第二百一十一期 發刊期一百一十年十月五日
|
||||
| ■回首頁 | ||||
|
|
||||
|
臺灣戲曲中心旗艦製作之回顧與分析 文•王子雍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劇藝發展組組長 臺灣戲曲中心自2017年啟用以來迄今,一直致力戲曲推廣與開拓,尤其在結合傳統形式與當代精神上的努力更不遺餘力。這些年來,中心先後推動「新作發表」、「戲曲夢工場」等等項目。然而,最受矚目的應屬由中心主導之年度旗艦製作,禀持「戲曲台灣」以戲曲述說台灣故事的宗旨,一棒接著一棒,截至目前已先後推出《月夜情愁》(2018)、《當迷霧漸散》(2019)、《雨中戲臺》(原訂2020推出,因疫情延至隔年2月)、《海賊之王──鄭芝龍傳奇》(2021年4月)等四齣。這四齣戲各有千秋,展現不同的風華與實驗,本文擬從比較的觀點,分析每齣戲的敘事手法,以及團隊面臨戲曲創新所採取的策略。 《月夜情愁》由唐美雲歌仔戲團製作,邱坤良編導。該劇以戲中戲的手法,述說著三段不同情境的愛情。除了舞台劇的成分,戲中戲的結構讓演出得以呈現北管西皮和福祿兩種不同的唱腔,以及再現結合影像與真人演出的連鎖劇,最後更透過改編自李漁之《憐香伴》傳奇,演出連鎖劇《憐香惜玉》裡的重要片段。各種不同的表演風格,既有歷史重現,亦有新編嘗試,造就了這一齣複雜的敘事結構:只因雙方家長屬於不同派別的北管傳統,一對相愛的年輕男女無法結合,與之相對的,則是戲班裡複雜的情感糾葛。如果說年輕人的遺憾來自環境阻撓,戲班裡的遺憾則是個人不同的情感歸宿。然而在《憐香惜玉》,趙香蘭、劉玉真之間唯美的愛情卻有完滿結局,似乎暗示著現實與虛構之間的差別,以及藝術(戲劇)能為苦悶現實帶來的昇華力量。在如此複雜的敘事結構裡,編據安排了「三聖士」,彷彿希臘悲劇的歌隊,亦如布萊希特的「說書人」,既在情境之中,亦在情境之外,既是攪和其中的雞婆,也是帶著批評的觀察者。他們的打諢插科充滿喜感,他們的反思則帶來審美的距離。 同樣地,說書人與戲中戲的結構也出現在《當迷霧漸散》,由一心劇團製作、李小平導演、施如芳編劇。然而,劇中的「辯士」所扮演的功能較之《月夜情愁》「三聖士」要吃重許多。對於劇中人物所面臨的困境,辯士時而同情,時而嘲諷;對於劇情的走向,辯士可為觀眾穿針引線,有時甚至以全知觀點,深入人物心裡。而且,當辯士和眾傀儡一同在舞台上互動時,他們是名符其實的悲劇歌隊了。四齣戲裡,《當迷霧漸散》的敘事結構最為複雜。劇裡,時序的跳脫沒有明顯交代,而且從現實到夢境,從夢境到回憶,從回憶到想像、從想像到史實等等,各個場景變換的界線刻意模糊,彷彿意識的流動。編劇透過豐富的想像力,生動地表達了林獻堂晚年滯日不歸的內在糾葛。同時,藉由戲中戲結構,本劇呈現各種不同的表演風格:舞台劇、歌仔戲、京劇、歌舞演唱等等。重要的是,這些風格的匯集有其內在肌里,有的根據人物的背景而來,有時則隨著人物的處境而起,緊密結合了外在與內在,從而造就了一齣別出心裁的新編戲曲。 《雨中戲台》由金枝演社、春美歌劇團共同製作、王榮裕導演、紀蔚然、劉秀婷編劇。有趣的是,它也有戲中戲的結構。若說《月夜情愁》主要情節繞著三段戀愛打轉,而《當迷霧漸散》聚焦於一個具代表性的個人對故鄉與親人的糾結情懷,《雨中戲台》則藉由述說一個小生演員的遭遇,同時展演歌仔戲起起伏伏的歷史。劇中的戲中戲,有時呼應主要人物的個人處境,但大半則呈現名小生跟著歌仔戲這個劇種經歷的過程。就敘事結構而言,該劇有兩條緊密交織的主線:小生演員和她兒子的關係為其一,歌仔戲從廟會、野台、電台、電視的發展為其二。同時,《月夜情愁》的「三聖士」和《當迷霧漸散》的辯士,到了《雨中戲台》變成了「志成」這個對著觀眾表白的敘述者。相對於保持距離的「歌隊」或帶來客觀視野的「說書人」,志成是個懺悔者,頗似田納西.威廉斯回憶劇《玻璃動物園》裡的湯姆(Tom)。然而,《雨中戲台》最大的特色在於試探、拓展「胡撇戲」的可能性。在上半場,表演形式時而舞台劇,時而歌仔戲,然而到了下半場,表演形式逐漸由胡撇戲取代,不但融合了舞台劇與歌仔戲兩種表演形式,也跳脫了戲中戲的敘事結構。 相較於之前三齣製作,《海賊之王──鄭芝龍傳奇》既沒說書人,亦無戲中戲。由明華園劇團製作、黃智凱編導,該劇以平鋪直敘的方式述說鄭芝龍崛起的過程。有別於《當迷霧漸散》於不知不覺中變換時空,《海賊之王》側重的反而是在觀眾面前迅速地變換場景,仿如影視的剪接技術。除了換場的噱頭以及各種特技的展演之外,這齣戲的特色在於編導著重的是「群戲」,而不是特定的人物(或演員)。另一個特色則是《海賊之王》打破了傳統戲曲裡善惡分明的道德觀,劇中沒有「才子佳人」,每個人物都在情勢逼迫下做出自己的選擇。總結而言,這是一齣技術甚於內容的製作。 四部劇作有三齣運用戲中戲結構,比例甚高。這個現象凸顯了新編歌仔戲所面臨的困境。若不想把時空侷限於「古代」,也不願安於改編舊戲,如何以歌仔戲為主體且又能與當代精神接軌,是劇作家最大的課題。就表演形式而言,前三齣都是舞台劇與戲曲的合成體,但只能稱之為輪番上陣的「混搭」,而非骨肉合一的「交融」。彷彿意味:劇作家在實驗「歌仔戲當代化」時,「戲中戲」既為美學「利器」,亦是不得不然的「柺杖」。在《雨中戲臺》下半場,胡撇戲的形式多少避開了時而寫實劇、時而歌仔戲的窘境。然而,設若胡撇戲可為解決之方案,它不應停留在過去的胡撇戲;諸如愛情與復仇主題,以及對於巧合與命運捉弄的搬演等等,皆已不合時宜;它需要重新思考、重新形塑(不只劇本,還包括造型、化妝、音樂與表演風格等等),否則又會陷入窠臼而無力建構新的美學。 當然,風格自由、不受時空限制的胡撇戲,只是許多選項之一。歌仔戲的拓展,同時涉及創造與破壞,「戲中戲」堪稱「安全牌」,如何擺脫這個包袱而大破大立,尚需藝術家更創新的思維和大膽的嘗試。 |
||||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禁止轉貼節錄 國光劇團 國光電子報 第二百一十一期 發刊期一百一十年十月五日 111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51號 電話:(02)88669600 發行人:張育華 藝術總監:王安祈 主編:黃馨瑩 執行編輯:林建華 c2003-2021 kk.gov.tw . All Rights Reserved.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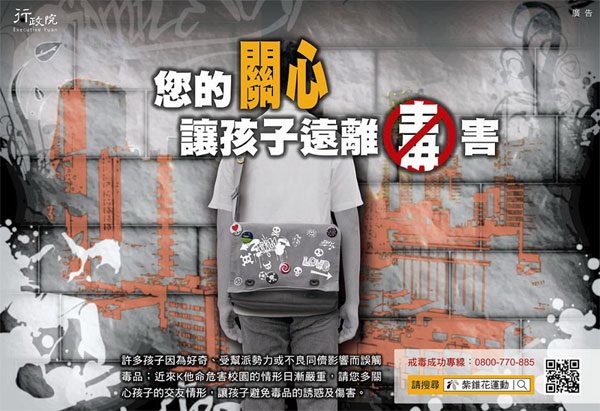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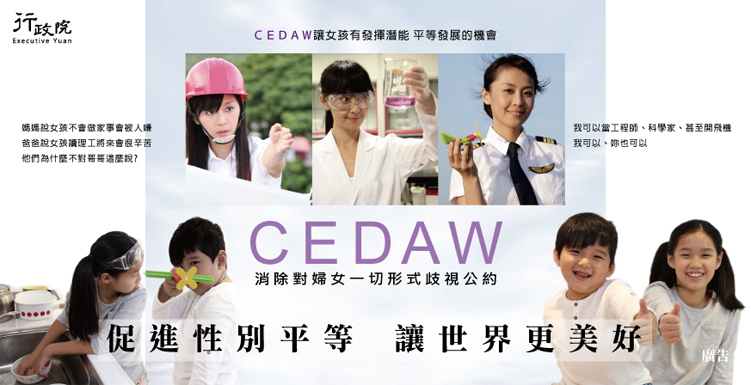 |
||||